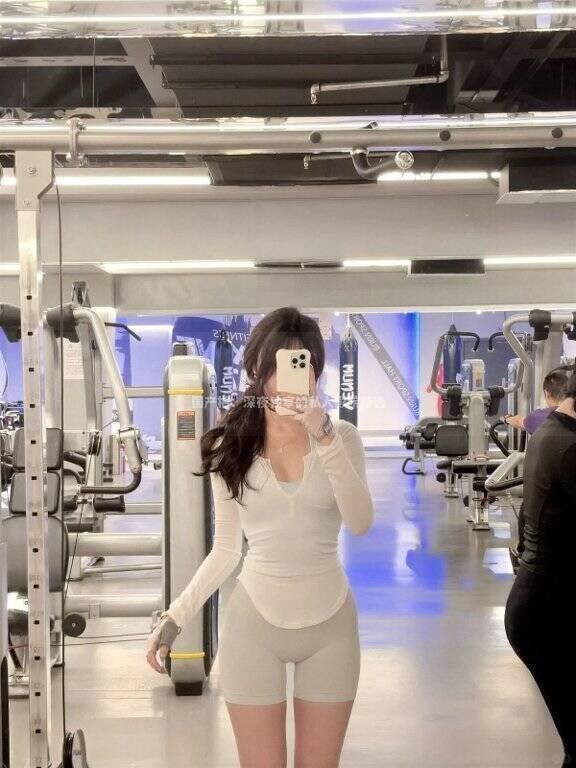视色
起初只是眼角余光里的一抹异样,像黄昏时分的云层边缘,被落日余烬烫出的那一道若有若无的金红,它并不在视野中央,却固执地停留在视网膜最敏感的区域,如同耳畔持续的低频嗡鸣,你知道它在那里,无法真正忽略,我试图将视线固定在面前摊开的书页上,那些铅字却开始游移、模糊,排列成毫无意义的黑色斑点,而那一抹色彩,在视野边缘,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加深、晕染,仿佛一滴墨在宣纸上无声地洇开。

我调整了坐姿,让脊柱更直一些,双手平放在膝头,这是一个防御性的姿态,却也是邀请——邀请那抹色彩更清晰地显现,呼吸被刻意放得绵长,胸腔的起伏降到最低,仿佛任何多余的动作都会惊扰这正在成形的幻象,它现在有了形状,不规则的,边缘毛茸茸的,像隔着毛玻璃窥见的一团暖光,颜色难以名状,不是光谱上任何单纯的色相,是记忆里某种熟透果实破裂瞬间的色泽,混合着体温与某种隐秘的甜腥,它并不移动,只是存在着,浓度在增加,像夜色一层层涂满窗玻璃。
喉咙有些发干,吞咽的动作变得异常艰难,仿佛喉间堵着一团温热的棉花,我能感觉到脉搏在太阳穴、在腕间、在指尖跳动,每一次搏动都像在将那抹色彩泵向更深的意识底层,它开始产生温度,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热,而是一种知觉上的暖意,从视野边缘悄然蔓延过来,贴着皮肤,渗入毛孔,指尖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,又强迫自己松开,不能触碰,甚至不能在想象中勾勒它的质感,必须停留在“观看”的层面,尽管这观看已变成一种全身心的、绷紧的汲取。
它似乎在变化了,不是形状或位置的变化,是“密度”的变化,从一团朦胧的光晕,逐渐向内凝聚,有了某种核心感,某种近乎“凝视”的意味,我感到自己正被它观看,这个念头像细小的电流窜过脊椎,背部的肌肉微微绷紧,肩胛骨向中间收拢,是一个既想退缩又想迎前的矛盾姿态,那色彩的核心深处,仿佛有更深的阴影在旋转,缓慢地,像深海看不见的涡流,它吸引着注意力,像悬崖边缘吸引着脚步,一种混合着眩晕的渴望在胃部深处轻轻搅动。
我闭上了眼睛,黑暗降临,但那一抹色彩并未消失,它烙印在眼皮内部的黑暗里,反而更加清晰、更加咄咄逼人,它现在是活的,随着我自身的血液循环在微微搏动,随着每一次心跳变换着细微的色调,从那种暖昧的果实色,转向更沉郁的、接近淤血的紫红,边缘又泛着缺氧般的青蓝,它在内部的空间里膨胀、收缩,像一颗不属于我的、沉默的心脏,我猛地睁开眼,它还在原来的位置,仿佛从未离开,只是变得更加“在场”,空气似乎粘稠起来,每一次吸气,都像在吸入被那色彩浸染过的微粒。
时间感消失了,可能是几分钟,也可能是一整个钟头在寂静中流走,房间里原有的声音——远处模糊的车流,暖气管道偶尔的轻响——都退到了意识的极远处,整个世界收缩为眼前这一方空间,以及空间边缘那一抹持续燃烧、持续低语的色彩,我与它之间,形成了一种绝对的对峙,一种静止的张力,没有故事,没有前因后果,只有这纯粹的、几乎令人难以承受的“正在发生”。
指尖传来麻痹感,沿着手臂向上爬升,我知道,只要一个极小的动作——转动眼球,甚至只是瞳孔一次不经意的颤动——就能让视线完全捕捉到它,让这边缘的窥视变成正面的遭遇,那个动作的诱惑力巨大无比,像舌尖即将触到盐粒前的刹那,全身的神经末梢似乎都指向了那个尚未做出的动作,积蓄着能量,等待着释放的指令,呼吸屏住了,悬停在吸与呼的中间点,胸腔里有一种饱胀的疼痛。
最终,我没有动。
那抹色彩,依然停留在视野的边缘,保持着它暧昧的形态与温度,它没有前进,也没有后退,我们之间,隔着一段精确的、令人发狂的距离,这段距离里,充满了所有未曾发生的故事,所有被克制在喉咙深处的叹息,所有在皮肤下奔涌却未曾破土而出的颤栗,它就在那里,一个永恒的“可能”,一个悬置的疑问,一个用全部感官去触摸却始终没有真正触碰的轮廓。
房间的光线似乎暗淡了一些,那抹色彩,也随之变得柔和,仿佛要融入渐浓的暮色里,但它没有消失,我知道,只要我再次凝神,它依然会在那里,在目光所及的边界上,静静地燃烧,静静地等待,而我的视线,依旧固定在正前方那片虚无的空气里,停留在那片令人心悸的、丰饶的空白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