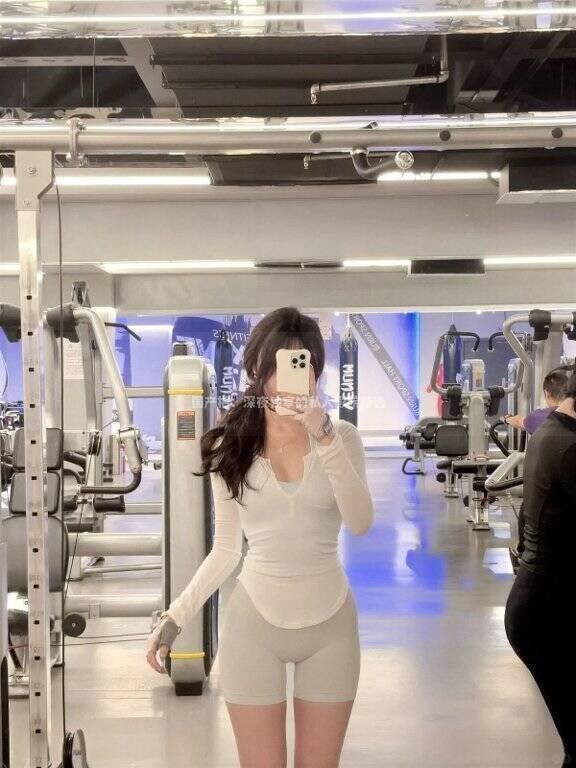鲁大妈
她总是坐在那张藤椅里,藤条的颜色已经暗得发黑,扶手处磨得油亮,每天下午三点,阳光斜斜地切过窗棂,刚好落在她膝盖上那块深蓝色的围裙上,围裙洗得发白,边角起了毛球,但她从不换下,她就那么坐着,双手交叠在围裙上,手指偶尔会无意识地捻着围裙的布料,捻得很慢,一圈,又一圈。
窗外的巷子很窄,对面人家的晾衣竿几乎要伸到这边窗台,晾着的衣服在风里晃,影子在她脸上游走,她的目光跟着那些影子移动,从左边墙上的水渍,移到右边窗台上的那盆仙人掌,仙人掌很久没浇水了,表皮皱缩着,但她不去碰它,只是看着,眼神空空的,又好像装满了什么沉重的东西,沉得让眼皮都微微下垂。

有时巷子里会有自行车铃响,她的手指会突然停住,停在捻到一半的动作上,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静止——不是放松的静止,而是绷紧后的突然凝固,像一支拉到满弓却忽然卡住的弦,呼吸变浅了,浅到几乎看不见胸口的起伏,她侧耳听着,听着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响,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,直到声音完全消失在小巷尽头,那口气才缓缓地、极其缓慢地吐出来,吐得很轻,轻得像怕惊动什么,然后手指继续捻动,恢复之前的节奏,一圈,又一圈。
厨房的水龙头有点漏水,滴答,滴答,每一声都落在特定的寂静里,她不去拧紧它,就让它滴着,那声音成了房间的脉搏,缓慢而固执,她的目光有时会移向厨房的方向,不是看,只是朝着那个方向,嘴角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,像是要形成一个表情,却又在半途消散了,最终什么表情也没有,只是唇线抿得更直了些,直成一道苍白的缝。
黄昏来得很快,阳光从膝盖上撤退,爬上围裙的褶皱,爬上交叠的手背,最后只停留在指尖,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,手背上的老年斑在渐弱的光里显得模糊,她动了动手指,极其缓慢地张开,又合拢,仿佛在确认什么,又仿佛只是无意义的动作,指甲剪得很短,短到几乎贴着肉,边缘修得整整齐齐,没有一丝毛刺。
巷子里传来孩子的笑声,尖锐而欢快,她的眼皮颤了一下,交叠的手突然收紧,指节泛白,但只持续了一瞬,很快又松开了,围裙的布料被攥出了新的褶皱,她用手掌慢慢抚平,抚得很仔细,从中间向两边,一下,又一下,孩子的笑声远去了,取而代之的是哪家厨房爆锅的刺啦声,带着油烟的气息飘进窗子,她的鼻翼微微翕动,不是闻,更像是被那突如其来的声响惊动,然后她闭上眼睛,闭了很久,久到让人以为她睡着了,但她的手指还在动,在围裙上划着看不见的图案,圆圈,或者直线,毫无规律。
天光暗到看不清手指的时候,她会动一动,先是脚,穿着布鞋的脚在地上挪了半寸,然后是腰,慢慢地从藤椅里直起来,起身的过程很慢,像一部生锈的机器重新启动,每个关节都发出细微的声响,站定后,她会望向窗外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巷子,望很久,黑暗里,对面窗户陆续亮起灯光,暖黄的,白炽的,一格一格,像被划分好的孤岛,她的脸映在窗玻璃上,模糊的,与窗外的夜色重叠在一起。
她转身走向厨房,步子很小,拖鞋摩擦着水泥地,发出沙沙的声音,经过饭桌时,她的手在桌沿停了一下,只是轻轻一触,就移开了,桌上很干净,只有一只白瓷杯,杯底留着深褐色的茶渍,她的目光掠过杯子,掠过空荡荡的桌面,然后继续往前走,厨房的灯被拉亮,是那种老式的拉线开关,咔哒一声,灯光昏黄,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,拉得很长。
水龙头还在滴水,滴答,滴答,她站在水池前,看着水流细细地流下,没有伸手去接,只是看着,看着水如何汇聚,如何落下,如何在池底溅开细小的水花,然后她伸手,不是去关水,而是拿起搭在池边的抹布,抹布半干着,她把它展开,对折,再对折,折成一个方正正的小块,动作很慢,很仔细,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。
巷子里有狗叫了两声,短促的,很快又停了,她手里的动作顿了顿,侧耳听着夜的寂静重新降临,远处有电视的声音,隐约的对话,听不清内容,只有嗡嗡的背景音,她垂下眼睛,看着手里折好的抹布,四四方方,边角整齐,看了一会儿,她把它放回原处,放在池边那个固定的位置,与池沿平行。
窗外的灯光又灭了几盏,夜更深了,她还在厨房里站着,站在昏黄的灯光下,站在滴水声里,影子在墙上,一动不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