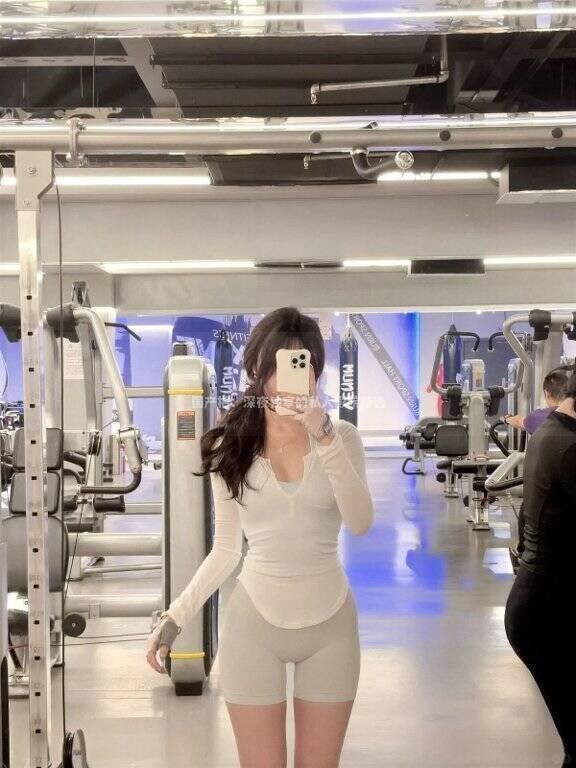不打码
指尖悬在发送键上方,微微发颤,屏幕的光映在瞳孔里,把整个房间都吸了进去,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一下,又一下,撞在肋骨上,闷闷的,像隔着厚布敲鼓,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,远处零星几点灯火,模糊成晕开的光斑,空气是凝滞的,带着晚春特有的、微潮的暖意,黏在皮肤上。
我知道那是什么,那几行字,躺在对话框的底部,像几枚静静蛰伏的、形状不规则的黑色石子,它们本身并无特别,只是寻常的词语排列,可我知道,一旦发送出去,它们就不再仅仅是词语,它们会变成钥匙,或者,更确切地说,变成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,我无法预知那涟漪会扩散成什么样,会触碰到哪一片我从未想过会触及的、幽暗的湖岸。
呼吸不自觉地放轻了,又似乎屏住了,胸腔里有一种奇异的饱胀感,仿佛吸进去的不是空气,而是某种密度更大的、无形的东西,喉咙发干,吞咽的动作变得异常清晰,能感觉到喉结上下滚动时,与衣领摩擦的细微触感,指尖下的按键,冰凉,光滑,带着一种近乎诱惑的、等待被按下的弧度,指腹能感受到那塑料壳体下,微不可察的弹性临界点——再往下一点点,只要一点点,就会听到那声轻微的、决定性的“咔嗒”。

我停住了,就停在那边缘上。
一种近乎自虐的清醒攥住了我,我看着那些字,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写下的密语,我逐字默读,试图用最冷静的目光去拆解它们,剥离所有可能附着的、多余的情绪色彩,可它们顽固地抵抗着这种拆解,每一个字都像有了生命,在屏幕的微光里轻轻搏动,边缘晕开模糊的光晕,引诱着,也抗拒着,我甚至能想象出对方看到它们时的第一反应——或许会是短暂的沉默,对话框顶端那“正在输入”的提示会闪烁又熄灭,再闪烁,又或许,什么都不会有,只是沉默,更长久的沉默,像投入深井的石子,连那一声回响都被黑暗吞没。
这悬停的片刻被无限拉长了,时间不再是线性的流淌,而是变成了一团粘稠的、胶着的物质,包裹着我,我能感觉到血液在耳膜里冲刷的声响,嗡嗡的,带着一种遥远的轰鸣,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像是被抽离了,只剩下这只悬停的手,和这双紧盯着屏幕、几乎要沁出泪来的眼睛,一种混合着恐惧与兴奋的战栗,从脊椎的末端悄然爬升,细密如蚁行,所过之处,皮肤泛起一层看不见的颗粒。
我为什么要写这些?这个问题像水底的暗影,倏地浮上来,又沉下去,没有答案,或者,答案就藏在那些黑色的字符里,但我拒绝去解读,我只是写下了它们,遵从了那一刻内心最直接、最不加修饰的冲动,现在,这冲动凝结成了实体,横亘在我与那个“发送”的动作之间,也横亘在我与之后所有可能的“之后”之间。
克制,这个词像一道冰冷的闸门,骤然落下,不是阻止,而是悬停,让一切可能发生的湍流,都暂时冻结在这道闸门之前,让所有呼之欲出的情绪,所有即将崩塌或建立的关联,都维持在这个将发未发的、极度脆弱的平衡点上,这是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,我品尝着这份清醒带来的、混合着微痛与奇异的掌控感,我掌控着这沉默,掌控着这未定的悬念,掌控着由我亲手创造、却又被我亲手按住喉咙的、这只言片语的命运。
指尖因为长时间的紧绷,开始传来细微的酸麻,那酸麻感沿着神经末梢,一丝丝地向上蔓延,提醒着我这具肉体凡胎的存在,提醒着我此刻正身处这个寂静的、被屏幕微光照亮的方寸之地,窗外的某处,似乎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夜鸟啼鸣,短促,飘忽,瞬间又被无边的寂静吞没,那寂静此刻有了重量,沉甸甸地压下来,压在我的肩膀上,压在我的呼吸上。
对话框静静地亮着,那几行字,依旧躺在那里,我的指尖,依旧悬在那里,发送键的轮廓,在昏暗的光线里,显得格外清晰,也格外遥远。
一切都准备好了,一切,也都还没有开始。
空气里,只剩下我自己的呼吸声,轻了,又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