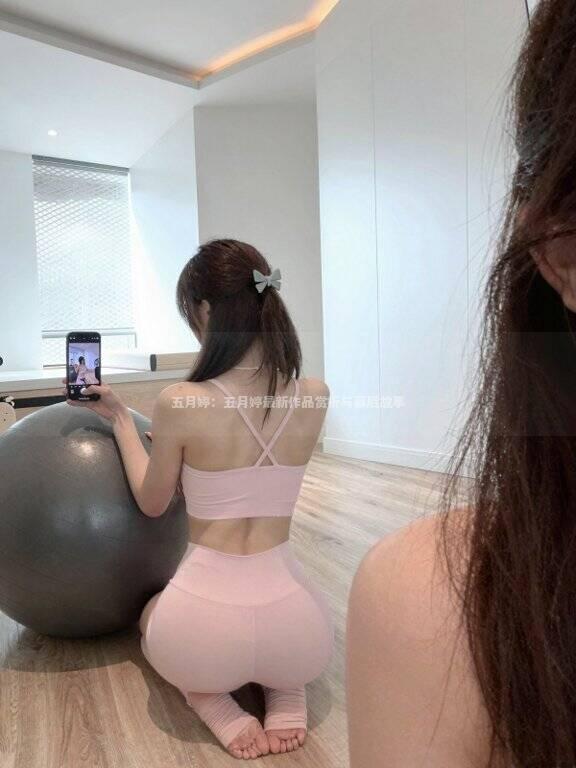一二三
她坐在榻榻米上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和服袖口的刺绣,窗外是东京的夜,霓虹灯的光晕透过纸拉门,在房间里投下暧昧的暗影,空气里有淡淡的线香味,混着某种她说不清的、更私密的气息。
“一。”她默念着这个数字,舌尖抵住上颚,然后轻轻松开,这是开始,也是结束,她想起第一次穿上这件和服时的笨拙,腰带缠了三圈才勉强系好,母亲在一旁摇头,说她还不够熟练,现在,她能闭着眼睛完成整套流程,手指在丝绸间穿梭时,甚至不需要思考下一个动作是什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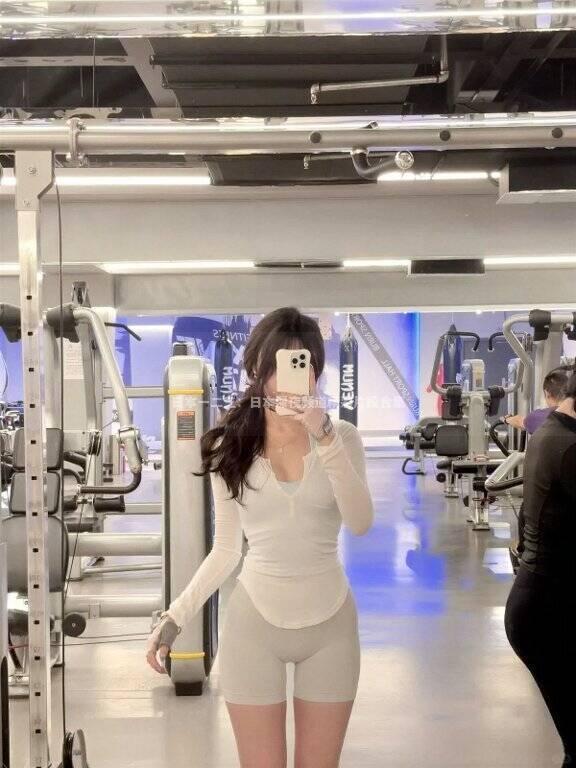
但今晚不一样,今晚的每一步都带着重量。
她听见走廊传来脚步声,很轻,但每一步都踩在她心跳的间隙里,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,指甲修剪得很整齐,涂着淡粉色的蔻丹,这双手今天下午还在插花,握着剪刀修剪山茶花的枝条,现在却微微颤抖,她把手藏进袖子里,又觉得这样太刻意,于是重新拿出来,平放在膝盖上。
“二。”第二个数字,过渡,中间状态,不上不下。
脚步声停了,就在门外,她屏住呼吸,等待,一秒,两秒,三秒——纸门被拉开的声音像撕裂了什么,她没有抬头,视线停留在榻榻米的纹路上,那些交错的草茎编织出复杂的图案,看久了会头晕。
他进来了,她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填满了房间的空白,空气突然变得稠密,他跪坐在她对面,隔着一段礼貌的距离,太礼貌了,她想,礼貌得让人心慌。
“茶?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比想象中平稳。
他点了点头,她开始准备茶具,手指触碰到冰冷的瓷器时,轻微地瑟缩了一下,热水注入茶碗,蒸汽升腾起来,模糊了彼此的视线,她喜欢这个瞬间,可以暂时躲藏,但蒸汽很快散去,一切又清晰起来。
她把茶碗推过去,指尖不经意擦过他的手背,很轻的接触,几乎算不上接触,但皮肤上却留下灼热的印记,她收回手,指尖蜷缩起来,藏在掌心。
“三。”最后一个数字,完成,或者,另一种开始。
他没有立即喝茶,而是看着她,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,像有实质的重量,从她的发髻滑到颈侧,再到和服领口露出的一小片皮肤,那里开始发烫,她希望灯光足够暗,暗到藏起她逐渐泛红的皮肤,但同时又矛盾地希望他能看见——看见什么?她不敢深想。
他说话了,声音很低,谈论着无关紧要的事:天气、茶的味道、最近看的一部电影,她应和着,声音飘在空气里,连自己都听不真切,她的注意力全在别处:他说话时喉结的滑动,他放下茶碗时手腕的弧度,他稍微调整坐姿时和服下摆的褶皱变化。
时间变得粘稠,每一分钟都被拉长,填满细小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张力,她注意到他茶杯边缘有一个极小的缺口,她的目光停在那里,无法移开,那个缺口成了一个锚点,让她不至于完全迷失在这种紧绷的寂静里。
他移动了,不是朝她,只是换了个姿势,但整个房间的气氛随之改变,空气里的线香味似乎突然浓烈起来,混着他身上淡淡的须后水味道,形成一种陌生的、令人不安的混合气息,她的呼吸变浅了,胸口有轻微的起伏,和服下的身体开始意识到每一层布料的摩擦。
他提到了什么——一个地名,一次旅行,某个夜晚的回忆,他的话语里藏着钩子,不明显,但足够让她捕捉到那些未说出的部分,她回应时,声音里带了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沙哑,这个发现让她心惊,于是她端起自己的茶碗,借喝茶的动作掩饰瞬间的慌乱。
茶已经凉了,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,她吞咽时,感觉到喉咙的收缩,颈部的线条随之牵动,她知道他在看,她知道他知道她在紧张,这种相互知晓在沉默中生长,像暗室里的植物,不见光却疯狂蔓延。
他的手放在了矮桌上,离她的手只有几厘米,她没有动,但全身的注意力都汇聚到那一小片空间里,皮肤变得异常敏感,几乎能感觉到他手指散发的温度,如果他再靠近一点——这个念头突然出现,带着不该有的清晰度,她咬住下唇内侧,用轻微的疼痛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窗外传来远处电车的声响,模糊的,像另一个世界的回音,这个房间与世隔绝,只有他们两人,以及这不断膨胀的、几乎有形体的沉默,她数着自己的心跳,一、二、三,然后又重新开始,循环往复,像某种没有出口的咒语。
他说话了,这次声音更轻,几乎像耳语,她不得不向前倾身才能听清,这个动作让和服的领口松动了些许,一丝凉意钻进衣内,她听见他的话,简单的词语,但排列方式让她指尖发麻,她没有回答,只是看着他的眼睛,在昏暗的光线里寻找某种确认——或者否认。
他的手指移动了,不是朝她,只是在桌面上画了一个看不见的圆,缓慢的, deliberate 的动作,她的目光追随着那看不见的轨迹,呼吸停滞在胸腔里,一圈,两圈,三圈,然后停住。
空气彻底静止了,连窗外城市的嗡嗡声都消失了,只剩下血液在耳中流动的声响,低沉而持续,她等待下一个动作,下一个词语,下一个呼吸——但什么都没有,只有这悬置的瞬间,无限延长,像拉至极限的弦,颤抖着,却还未发出声音。
她的手指微微张开,又合拢,丝绸袖口摩擦皮肤的声音被放大,沙沙的,私密的,她看见他的目光落在她的手上,然后缓缓上移,经过手腕,小臂,肘部——尽管那里被布料完全覆盖,视线是有重量的,她此刻无比确信。
茶碗里的最后一点茶水映出头顶灯光的倒影,微微晃动,整个房间都在微微晃动,或者只是她的错觉,她不确定,唯一确定的是膝盖上紧握的双手,指甲陷入掌心带来的钝痛,以及喉咙深处那种干燥的、渴望什么的焦灼感。
他动了,不是大的动作,只是肩膀放松了一毫米,呼吸稍微深了一些,但这个微小的变化像石子投入静水,涟漪扩散到她所在的位置,她的脊背挺直了一些,又强迫自己放松,结果变成了一种不自然的僵硬。
远处传来钟声,模糊地数着时辰,她没去数是第几声,只是听着那声音逐渐消散在夜色里,像糖在水中融化,不留痕迹,留下的只有这个房间,这两个人,这段距离,这个夜晚。
她的舌尖掠过上颚,准备说出什么——一个词语,一个音节,一个呼吸——但在成形之前就消散了,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沉默,更重的空气,更尖锐的期待,和服的腰带似乎比平时更紧,束缚着每一次呼吸的起伏,她想着要不要调整一下,但这个念头本身就像一种背叛。
他看着她,她也看着他,目光在空气中交缠,却没有真正接触,像两艘夜航的船,在黑暗的海上保持距离,只凭灯光知晓彼此的存在,灯光闪烁不定,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,在雾中明明灭灭。
她的手终于移动了,不是朝他,只是调整了一下茶碗的位置,让那个缺口转向另一边,这个动作花了太大的力气,完成后她几乎要叹息,但忍住了,叹息会泄露太多,而今晚的一切都关于未泄露的部分——那些在皮肤下涌动,在呼吸间徘徊,在目光中闪烁却从未说出口的一切。
线香燃尽了,最后一缕青烟盘旋上升,然后消散,气味还在,但失去了源头,变成房间里记忆的一部分,就像此刻正在发生的一切,正在变成记忆,即使它还远未结束——或者,正因为还远未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