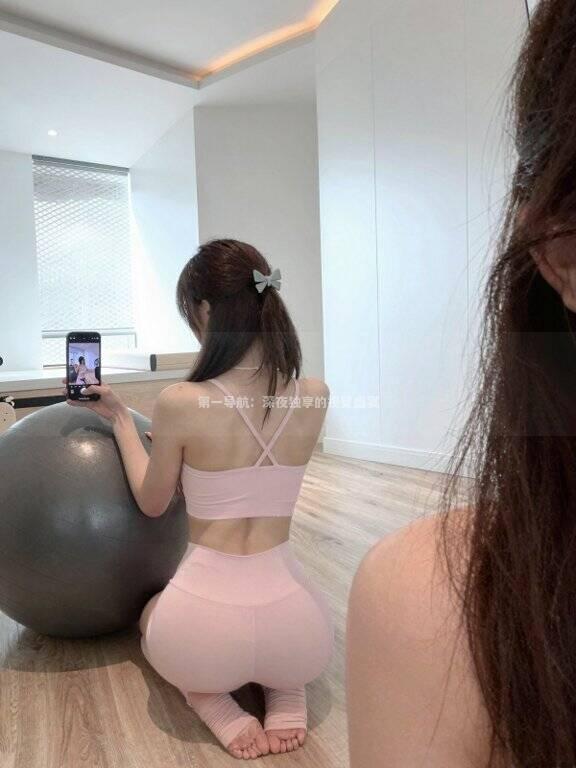秋霞电影院
他推开那扇沉重的玻璃门时,门轴发出一种被遗忘的呻吟,冷气像薄纱一样贴上来,不是商场里那种蛮横的、要将人骨髓都吹透的冷,而是一种缓慢的、带着灰尘气味的凉意,从脚踝开始,一寸寸向上爬,售票窗口空着,玻璃上贴着褪了色的手写影讯,墨迹晕开,像被雨水打湿的梦,他站在那里,没有喊人,只是看着那空荡的窗口,空气里有种黏稠的静,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时那种低沉的嗡鸣,还有远处放映厅隐约漏出的、被墙壁闷住的对话声,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。
他走向二号厅,走廊的壁纸是暗红色的,印着模糊的缠枝花纹,许多地方已经剥落,露出底下更陈旧的底色,壁灯的光是昏黄的,只勉强照亮脚前一小块地毯,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,行走变成一种无声的悬浮,他推开二号厅厚重的隔音门,更深的黑暗与更浓的旧时光的气味涌出来,将他吞没,银幕亮着,正演到一处安静的对话,蓝荧荧的光浮在空气里,照亮前排稀疏的、一动不动的头颅轮廓,他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,天鹅绒的椅面冰凉,且微微下陷,发出细微的、承受重量的叹息。

电影的情节他并不关心,那只是光影与声音的背景,他的注意力全在身侧空着的那张椅子上,椅子的扶手与他座位的扶手之间,有一道窄窄的、冰冷的金属缝隙,他的左手就放在自己这边的扶手上,指尖能感觉到天鹅绒磨损后露出的、略微粗糙的底布,他的余光,不受控制地,总落在那空椅子的扶手上,那里光滑,完整,覆着一层均匀的、无人触碰的灰尘,在银幕变换的光里,偶尔闪过一丝极微弱的亮,他想象另一只手放在上面的样子,指节的位置,皮肤的溫度如何慢慢焐热那一小块区域,但这想象只进行到一半,便像触到某种无形的屏障,倏地缩了回来,他不能想得太具体,具体是危险的,他只能让那念头悬在那里,一个模糊的、没有形状的轮廓,停在边缘。
银幕上,男女主角在雨中奔跑,笑声和雨声混在一起,很热闹,但那热闹是他们的,这里的静,是这里的,静是有重量的,压在他的胸口,让呼吸变得又轻又缓,每一次吐纳都小心翼翼,怕惊扰了什么,他感到自己的心跳,在胸腔里,一下,又一下,沉稳得有些过分,像在丈量这寂静的深度,偶尔,前排有人轻微地挪动身体,旧座椅的弹簧发出喑哑的“吱呀”一声,那声音在空旷的厅里被放大,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突兀,旋即又被更深的寂静吞没,每一次这样的声响,都让他肩膀的肌肉无意识地绷紧一瞬,再缓缓松开,绷紧与松开之间,有一种极其细微的、几乎无法察觉的战栗,顺着脊柱爬上去。
他想起一些碎片,不是连贯的画面,而是感觉:夏日午后灼人的阳光,柏油路面蒸腾起的扭曲热气,冰棍在手里融化,黏腻的糖水滴在指尖,还有声音:蝉鸣,尖锐得刺耳,却又在某个瞬间戛然而止,留下真空般的寂静,这些碎片没有来由,也不指向任何明确的过往,只是突然浮现,带着彼时鲜明的温度与触感,与此刻影院里恒久的凉意形成尖锐的对比,他任由它们浮现,又看着它们像水汽一样在意识的边缘蒸发,不去捕捉,不去串联,捕捉是向内的沉溺,串联是走向某个终点的企图,而这两者,都是他现在必须避免的,他只是在感受这些“浮现”本身,感受那种突如其来的、细微的情绪涨潮——或许是怀念,或许是别的什么——在它即将漫过某个阈值的瞬间,轻轻移开注意力,转向银幕上无关紧要的一个空镜头,或者天花板上某块颜色略深的污渍。
时间在这里失去了线性,它不再是向前流淌的河,而是弥漫在空气中的雾,缓慢地旋转、沉降,影片似乎到了某个高潮段落,配乐变得激昂,鼓点敲打着耳膜,但那激昂也是隔着一层的,像从很远的水底传来的震动,他的手指在扶手上,极其缓慢地,移动了大约一厘米,指尖划过磨损的天鹅绒,发出几乎听不见的“沙沙”声,就这一厘米,不能再多,这一厘米的移动,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带来一种虚脱般的、奇异的平静,移动之后,是更长久的静止,仿佛那一厘米,不是为了靠近什么,只是为了确认自己还能移动,确认那道冰冷的缝隙依然存在,确认“停止”本身,是一种主动的选择。
不知过了多久,身侧似乎有了极其轻微的空气流动,不是风,只是某种存在感临近时,空间本身的微妙调整,他没有转头,颈部的肌肉僵硬着,维持着直视前方的姿态,眼角的余光里,那片空椅子扶手上的灰尘,光线似乎暗了一下,又亮了一下,也许只是银幕上场景切换,也许不是,他的呼吸停了一拍,就那么悬在半空,肺部保持着半满的状态,有点钝痛,他让那口气极其缓慢地、无声地吐出来,仿佛吐出的不是空气,而是某种有形的东西,吐尽之后,并没有立刻吸入下一口,他在那短暂的、真空般的屏息里,等待着,等待什么呢?他不知道,或许只是等待下一个不可避免的呼吸动作的到来。
影厅里的光,似乎又暗了一些,影片可能临近尾声,也可能是电力不稳,那蓝荧荧的、浮动的光,变得稀薄,阴影从角落开始蔓延,像墨滴在清水里缓缓化开,黑暗变得更具实体,包裹上来,带着比之前更甚的凉意,前排观众的轮廓,渐渐模糊,融入背景,寂静更深了,深得像一口井,他依然坐在那里,左手放在扶手上,指尖停留在那一厘米移动后的位置,身侧的空气,那流动的感觉似乎还在,又似乎从未存在过,一切都被放大了:自己的心跳,旧空调系统低沉的喘息,远处街道上偶尔碾过的、闷闷的车轮声,一切又都被推远了,隔着一层厚厚的、透明的膜。
银幕上的故事,终于走到了结尾,演职员名单开始滚动,白色的字幕在深色的背景上缓缓上升,伴随着舒缓却略带感伤的音乐,影厅顶部的几盏小灯“啪”地一声亮了,光线微弱,昏黄,非但没有驱散黑暗,反而给一切蒙上了一层陈旧、疲惫的色调,前排的人开始窸窸窣窣地起身,模糊的影子晃动着,向出口挪去,他没有动,目光落在那些向上滚动的、陌生的名字上,却一个也没有看进去,音乐在继续,灯光昏黄地照着,身侧的椅子空着,扶手上的灰尘,在刚刚亮起的顶灯下,似乎看得更清楚了些,门轴转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,有人出去了,带进来一丝外面世界溼热的、含着夜气的风,但那风很快就被影院内部的凉意吞噬、同化。
音乐声渐渐低下去,低到只剩一丝游丝般的旋律,缠绕在空旷的座椅之间,滚动名单接近尾声,屏幕的光开始明灭不定地闪烁,他依然坐在那里,保持着那个姿势,仿佛成了这陈旧影院的一部分,成了这昏黄灯光下,一个静止的、等待被时间覆盖的剪影。